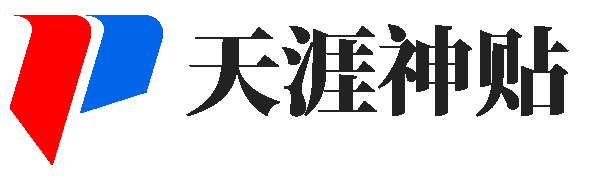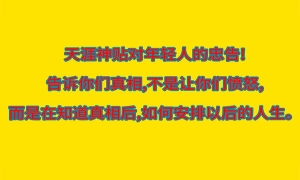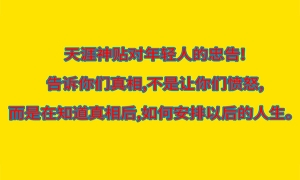-
-
生孩子过程的记录片播放给北里大学药学部的学生观看。
在药学部里面,女生占了六成,比较多。当我询问学生们观看这个节目后的感想时,得到的结果非常有趣。男生和女生的反应截然不同。
大部分看了这个节目的女生的感想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有很多新的发现。”另一方面,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男生们异口同声地说:“都是一些在保健课上就已经知道的东西。”观看同样的东西,男生和女生却得出了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既然来自同一个大学的同一个系,至少在知识水平上,这些学生之间应该是不存在太大差异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呢?
答案在于看待信息的角度——男生不想感受生小孩的真实感觉。因此,与其说男生看相同的记录片,不会产生女孩子那样的发现,倒不如说他们不会积极地去发现。
也就是说,对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他们会主动地隔断信息。在这里存在一堵墙,这就是“傻瓜的围墙”。
这段故事表明了人们在认识事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性。一起观看相同的记录片,结果男生说“全都知道”,而女生认真地看了细节后却说“有了新的发现”。很明显,男生并没有认真地看细节的部分,而只是随便地说“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平日里,我们会很容易地就说“知道了”。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看记录片时男女反应的差别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一章 什么是傻瓜的围墙认为自己“本来就知道”是一种很可怕的心理
“常识”不是指“人们知道的东西”,而是指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可问题是,即便是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未必人人都知道,所以如果有人因为某件事情是常识,就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的话,那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男女学生在看完记录片之后的差异表现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因为每个女孩子都认为自己也会经历生小孩的整个过程,所以她们会很认真仔细地看记
录片。如果将自己置身其中,她们就会切身地感受到片中的孕妇所经历的痛苦及喜悦,因此她们对每个细节都很感兴趣。相比之下,男生们的态度则是“知道不知道无所谓”。对于他们来说,眼前的画面只不过是重复一下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而已。事实上,当有很多未知的场面或信息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男生们往往连看也不看就说“已经知道了”。
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却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这是很可怕的。
第一章 什么是傻瓜的围墙知识和常识是不同的
像这种很简单地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的学生,常常会很轻易地来对老师说:“老师,请您解释一下……”但是,很多事情往往不是仅仅用语言就能说明白的。老师经常会以说教的形式向学生传授知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难教的就是那些总是说“请您解释一下”的学生了。
当然,我并不是否定语言的交流功能。但是实际上,好多事情都是无法单单靠语言传达
的。许多人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只要听了就能明白”,“只要别人说了自己就能弄懂”。
对于这样的学生,我有时会说:“我可以简单地解释一下,但是,你们能够体会出阵痛到底是怎样一种痛吗?”当然,女性是可以亲身体会到阵痛的,男性却体会不到。但即使这样,在真正看了生小孩的场面后,这些男生也都体会到了这种痛楚。不管怎么说,这些现场录像至少比医学保健书等教科书传达得更加直观。
好多人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他们总是认为,无论任何事情,别人简单地“说明”后,自己就能够明白,这是非常奇怪的!
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很多事情,即使别人说明了之后,自己也未必能够真正明白。相反,他们相信自己“看了电视之后就明白了”或者“拼命地看足球,就能明白到底什么是足球”。但事实上,他们甚至都没搞清楚什么是“懂得”或者什么是“明白”。
记得有一次,评论家彼得·布拉肯①对我说:“养老,日本人不认为‘常识’是‘杂学’吗?”我想都没多想,就大声回答:“是啊,就是这样子啊。”当时确实很得意。
在日本,有太多的人不明白“懂得一些东西”和“拥有一些比较杂的知识”完全是两回事儿。看生小孩的录像片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那些男生们仅仅因为在保健课上学到了一些“杂学”,就认为自己已经“明白”了。从这种意义上讲,“很有诚意地沟通就该能让双方都明白”这种误解的产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第一章 什么是傻瓜的围墙什么是现实
如果再进一步地想想什么是“明白”的话,我们就会遇到“到底什么是现实”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知道“已经明白了”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人对于“到底什么是现实?”这个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人有的时候会忘了自己身在何方,记忆也变得非常模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尤其是古人,并不知道这个世界原本就存在着一些不可解的东西。这种在现
实中的迷失,也正是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莽丛中》和电影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所反映的主题。
但问题是,现在已经渐渐没有人怀疑自己是否真正了解某些事物了。大家都会非常盲目地认为“自己对现实世界知道个大概”或者是“只要想知道,自己就能够知道”。
因此,很多人仅仅在电视上看到2001年9月11日纽约发生的那件事情,就认为自己已经“知道”、“明白”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两架飞机突袭了双子大楼,结果大厦倒塌了而已。
但是,电视和报纸并不能向我们传达全部信息,我们有好多细节都是一知半解的,和当时在场的人们所体会到的真实感觉完全两样。比如说,在场的人体会到的那种恐怖就是电视所不能传达的。尽管如此,虽然仅仅听到新闻,但还是有很多人以为自己对这件事什么都明白了。这种不承认自己在认识上的局限性的心理真的非常可怕。
可问题是,把真实的细节都弄明白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
现实中并不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人类才想知道确定的东西。因此他们发明了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宗教,我想他们都是在“现实这个东西十分模糊”的前提下成立的。
总之,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完全把握人类不明白的现实细节的,只有一个人:“神”。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前提,人类才有可能相信“凡事都有正确答案”。因此,他们才能够在科学领域中坚持不懈地寻求正确答案。正因为有惟一的绝对的存在,才会有绝对的正确答案。
日本人本来居住的地方,是有成千上万个神的世界。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钻牛角尖地追问“到底什么是真实”,或者“什么是事实”。因为,众所周知,“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一神论的世界和自然宗教的世界,即欧美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同日本社会之间的最大区别。
第一章 什么是傻瓜的围墙NHK是神吗
我认为“客观事实是存在的”这一观点还是存在于信仰领域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归根结底,这样的观点是任何人都无法确证的。然而最可怕的是,在如今的日本社会,人们并不知道这种观点只是属于一种信仰——他们把它当成了真理。
我一直认为NHK就是个典型代表。它以“公平、客观、中立”来标榜自己的报道。可我想对它说:“这是不可能的。怎么能够这么说呢?你以为自己是神吗?”如果它承认自己
不是神,那我还想问:“你到底是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还是犹太教徒呢?如果都不是的话,为什么你会非常自信地说自己的报道是‘公平、客观、中立’的呢?”
轻易地相信这样的口号实际上是十分恐怖的事情。因此,当对于政治家(比如说铃木宗男)的贪污问题产生疑惑的时候,人们会首先下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那个家伙是个坏人。就这样。”然后在定罪后再进行报道。这种做法非常明确地引起了思考的停止,可人们却没有发觉。
彼得·布拉肯所说的“常识和杂学混同在一起”,就是指这样的状况。事实上,“常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它并不是“杂学”的简单罗列,二者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把二者混淆。
那么,常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16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蒙田①所说的“常识”,简单地说,就是“任何人都会认同的东西”。虽然“常识”的内容不一定绝对地真实,但我们应该可以说,“常识是任何正常人都会认同的”。
蒙特利尔说:“有时候,人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别人的世界里却未必如此。”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人们当然就不会盲目地相信所谓的“客观事实”了。这就是真正懂得“常识”的表现。
第一章 什么是傻瓜的围墙科学的怪诞
那么,我们应该对“科学”抱有一种怎样的态度呢?也许会有人认为“虽然养老说得有些道理,但是科学的世界总应该有绝对的事实吧”。
虽然我并没有统计,但是科学家中大概有九成的人都相信“真相存在于科学之中”。要是一般的人,或许会更相信科学是绝对的。但事实完全不是这回事儿。
比如,最近我们总说“全球变暖是由二氧化碳增加引起的”,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了真理。不仅学者,就连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也将其作为一个既成的确定事实来不断地讨论。但事实上,这其实只不过是众多说法中的一个罢了。
在“地球逐渐变暖”这个问题上,能说得上是“事实”的,只有近年来地球的平均温度每年都在不断上升这一现象。至于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断增加等等,至多也不过是人们在“地球逐渐变暖”这一问题上的一种推论罢了。
而且就温度上升这个问题来说,它本身虽然是事实,但要说从以前开始一直就是直线上升的话,那也是不能确定的事。因为也有可能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处在气温上下波动中的上升部分。
最近我出席了林野厅①和环境部的茶话会。席间,大家就日本在执行最近签定的《京都议定书》的政策,以及如何获得国家预算,并逐渐加强对山林的治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那时给我们进行讨论的话题的题目是“由二氧化碳增加引起的地球变暖将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我提议将其改为“预测由二氧化碳引起的地球变暖”,却立即遭到一位在场官员的反对。他认为“国际上80%的科学家都承认,二氧化碳的增加是地球变暖的原因”。②但是在科学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行不通的。
我当场告诉他:“你的这种考虑方法是很令我担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恐怕这是行政部门第一次大规模地接受一个科学预测并依据其采取一些措施。如果后来发现采用的这个预测是错误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特别是就行政部门来说,它一旦采用了某种东西,就会顽固地坚持到底。所以说,简单地将科学预测认定为真理是非常可怕的。
科学的事实和科学的预测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就拿地球变暖来说吧,“气温在不断上升”是科学的事实;而说其原因是“二氧化碳的增加”就只是一个科学预测了。在考虑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进行这种简单的推测呢?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这种将事实和预测混为一谈的大有人在。不过如果严密一点来说的话,就连事实本身也只能被看成是一种解释。
第一章 什么是傻瓜的围墙科学中的反证很必要
维也纳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不能被反证的理论就不能被称作科学的理论”。人们一般把这种观点称为“反证主义”。
例如,如果要证明一个看上去非常正确的理论,单纯搜集好多与这个结论相一致的资料、数据是毫无意义的。想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命题,发现很多天鹅都是白色的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研究者证明了“黑色的天鹅不存在”之后,这个命题才能被称做是
科学的理论。
也就是说,真正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不能仅靠一些正面的论证就认定某一命题是绝对的事实,而是要承认其中存在可能被反证的地方。
比如说进化论吧,自然选择学说脆弱的地方就在于它不能被反证。就算你说“能够生存下来的都是适合生存的”,别人也没有办法进行反证。因为那些没有被选择而无法生存下来的生物都已经不存在了。
不管你进行了多么合理地说明,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推论的结果罢了,因为实际上,你并不能证明“不能生存的生物就一定不能适应环境”。
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举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反证。他思考了这个理论能否通过实验检验的问题,并对爱因斯坦所说的“空间是弯曲着的”这一说法①提出了质疑。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曾经有人在日食的时候观察过星体的位置。结果他看到了那些实际上被太阳遮住的星体,也就是说光是曲折地传过来的。这就成为“空间是弯曲着的”这一理论的证明。所以,波普尔说,越在一件事情上就能见分晓的理论越是一个经得住推敲的好理论。
第一章 什么是傻瓜的围墙什么是确定的呢
我上面所说的东西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误解,他们会提出“那么岂不是什么都不能相信了吗”之类的疑问。可是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武断的说法,没有一点科学的根据。
我从来没有说过“没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这种话。因为事实上,人类一直在不断地探索“确定的事实”。但正因如此,我们才要不断地怀疑、验证。跳过这些过程而武断地认为这世界上“存在着不变的事实”是一种类似文字游戏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那些提出这类疑问的人都会确信一件事:今晚回家的时候,自己家的房子一定还在那里。并不是说他们家房子没有因为失火而被全部烧毁的可能。而是所有这些事情都只不过是概率的问题。因为感觉“什么都不可信赖”而抱头苦恼是没有一点必要的,这种不安定的心态有时甚至会让人们陷入盲目的宗教信仰。
我并不是说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就鼓励大家什么都不要相信。认为地球变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二氧化碳引起的是可以的。就像每天的天气预报中说“有50%的降水概率”一样,大家都很平常地接受了。那么同样地,认为地球变暖80%是由二氧化碳引起的也是可以的。
但我们必须懂得,那种说法只是一种推测,而不是真理。为什么要坚持这么说呢?因为除了地球变暖这一问题之外,今后行政部门与科学的关联很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时侯,如果官员们将科学当做绝对的事实来盲目信任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导致非常危险的结果。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科学并不是一种社会信念。社会信念可以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科学并没有这个必要。
第二章 头脑中的系数头脑的输入输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在跟那些对不想知道的事情从来不听的人交谈时,你会感到自己很难跟对方沟通。将这个原理推而广之,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所有战争、恐怖事件以及民族、宗教间的纷争。例如,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矛盾虽然说很大,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对立的根源还是因为无法沟通。
让我们试着从人脑的角度分析一下,即从脑的输入输出问题上考虑。不用多说,脑的输
入是指信息进入脑内的过程,脑的输出则指人脑对输入的信息做出的反应。我们用五官来输入信息,最终输出的是一种意识。具体地说,脑的输出是一种运动。
我们这里所说的运动并不是指体育运动,说话是一种运动,写字是一种运动,动作表情等也都是运动,或者进一步说,对输入脑中的信息反复思考也可以被看成是脑的一种运动。
在与他人交流的时候,脑的输出就成为一种比较明显的运动。
第二章 头脑中的系数头脑中的一次方程式
那么,在从五官输入到由运动系统输出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大脑在干些什么呢?它在对输入其中的信息进行处理。
如果将这种输入称为x,输出称为y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整个信息处理的过程描述为y=ax这个一次方程式。也就是说,输入的信息x,在与脑中的系数相乘后,就会得出结果y。
那么这个系数a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可以把它叫做“现实的解释”。而事实上也存在着因为输入的信息不同,其结果也不同的情况。通常情况下,有一个什么样的x输入,人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说因为y存在,所以a就不是0。
但是也有a=0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输入什么,都没有结果输出,也就是说信息x的输入并没有对这个人的行动产生任何影响。
不对行动产生影响的输入通常对被输入的人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男生对“记录生孩子过程的录像”几乎没有什么感想,那是因为对于这个输入,他们的系数a=0(或者是一个和0无限接近的值)。因为他们不会面临生孩子的问题,所以也不会产生什么感想。
第二章 头脑中的系数虫子和百元钱
同样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不管阿拉伯人怎么说,甚至世界如何批判,他们对于这种信息输入的系数都是0,所以别人的批判对他们的行动毫无影响。
同样,对于以色列人的主张,阿拉伯人的系数也是0。因为虽然他们好像是在听,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听。换句话说,对于系数为0的一方来说,对方所说的那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再来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例如,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脚边有虫子在爬的话,我会停下来看看。但是没有兴趣的人就会完全忽视它,甚至看都不会看到。这就是说,对于虫子这个信息,那个人的系数是0。
但是,如果脚边有一个百元硬币的话,他也许就会停下来。如果是赛马券的话,他也许会想“说不定能中呢”,然后满怀期待地停下并捡起来。当然,如果是赛马券的话,我是不会停下来捡的。
有一种人的输出一点都不会受到输入信息的影响,而另一种人受到的影响则非常明显。不同的人对同一现实做出不同反应,这实际上也就是a值不同所造成的区别。
第二章 头脑中的系数无限大是绝对主义
日常生活中,a=0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有的孩子一点都不听父亲的说教。父亲把“好好整理自己的屋子”、“好好做作业”之类的话说了一大堆,孩子虽然当时说“知道了,知道了”,可也只是一种应付,实际上根本没听,所以第二天还会照常做那些不好的事。
在面对父亲的说教的时候,因为孩子的系数a=0,所以不管输入多少信息,都不会对他的行动产生任何影响。只有当“父亲生气了”这个信息输入大脑的时候,孩子才会做出反
应,比如说在看到父亲生气的样子后赶快溜掉。对于孩子来说,只有“父亲生气了”是现实,而父亲的说教则根本不是现实。
另一方面,与a=0相反,a也有等于无限大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就是绝对主义。
对于绝对主义者来说,有些信息、信条是绝对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与其相关的东西对他的行动起着绝对性的支配作用。自己尊敬的老师所说的话,安拉真神的语言,圣书上记载的信息等支配着他们的一切。当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的a是无限大的。
第二章 头脑中的系数感情的系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次方程式能够解释人们大部分的行为。前面谈的虽然都是关于“理解”的问题,但我们也可以同样用它来对“感情”问题做出解释。
简单来说,a为正的时候就是正面的、喜欢的,a为负的时候就是负面的、讨厌的。在见到某人的时候——视觉信息x输入的时候——如果a为正的话,那么行动y也就会是积极的、正面的。
无论是谁,如果见到自己亲近的人或是恋人的话,一般都会非常高兴地去接近或者微笑吧?但是如果见到的是自己讨厌的人或者是来要账的,那么a就会变成负数,作为结果的y自然也是负数,你可能就会像逃跑的兔子一样溜掉,殴打对方或是做出很讨厌对方的表情等,总之就是会采取一些负面的、消极的行动。
行动有正面行动和负面行动之分。也就是说,a有可能是+10,也有可能是-10。大脑就是这样运转并导致一定行为的。
从感情方面来说,美国人在看到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本·拉登的时候,因为负面的系数很大,所以就会非常生气甚至痛恨。但与此相反,虽然是看到同一个人,本·拉登的追随者的系数就应该是正的,所以他们心里就会产生很大的正面效应。
一般来说,在批判某人的时候,批判者心里的负系数通常是很大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是真心地批判的话,批判者至少会将批判对象作为现实的存在来看待。
也就是说,批判者的a并不等于0。正因如此,他的行动才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说憎恨、讨厌等情绪产生的前提都是将信息作为现实的存在。
第二章 头脑中的系数适应性是由系数决定的
想一下男女关系的问题,你就很容易理解以上的说法。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自己和一个一直讨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交往起来了。这和谚语中所说的“讨厌也是喜欢的过程”是很相似的。
简要地说,这种情况就是将a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而在a=0(即毫不关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变成这样的。因为那样的话,一个人就会对另一个人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兴趣,并没
有把对方当做现实来看。所谓“不在视线之内”(不在考虑范围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根据a值的大小,基本上就能确定一个人是否能适应某种环境。当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如果他的a值适合的话,这个人就有对环境的适应性,反之,他就不能适应那个环境。
“无论如何跟这个公司就是合不来,所以只好辞职”这种说法,实际上反映了这个人的a值和他所属的公司不能相适应,或者说他没有设定一个很好的a值。
当然,对于不管去哪个公司都很快辞职的人来说,也许他对所有公司发出的信息都没有设定一个很合适的a值。和将父亲的说教当做耳边风的孩子一样,那些对于上司的命令一直用0的系数来反应的年轻人大概根本不适合去公司上班。
在交流过程中,就算a为负值,也总比为0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有负数存在就说明还有挽救的可能。对于公司来说,如果员工的系数是0,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负面的东西积攒多了,就有可能突然转化成正面的东西。宗教中就有负面东西能够转化成正面的理论。基督教教义中所说的“浪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某个机会,比如说与神相遇,-10会突然转化为+10。
另一方面,有些人会利用宗教,使信徒也成为绝对主义——即a成为无限大的可能,他们借此会强烈要求“绝对的真理”,进而发展成为恐怖主义。原因就在于,系数无限大的人根本不可能与他人进行交流。
这种a为0和a为无限大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都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恐怖主义就是系数无限大的一种表现。过去曾有日本青年军官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问青红皂白就杀人的事。
平常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很少有走到那么极端的。如果一个人的系数为0或无限大的话,他就根本无法维持社会生活。但是在数学上,人们有时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例子,而且从理论上讲,我们有可能对于存在的事物丝毫不加考虑,所以还是要考虑系数为0和无限大的问题。两种情况大体上都会导致不好的输出,即不好的结果。
基本上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的“人类的社会性”就是要把a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值,这样这个人就能尽量适应多种状态。当然其中a为0才是正确系数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在街上走的时候,一直对电线杆做反应也是毫无意义的。
最近经常听到“情商”这个词,简而言之,就是感情、情绪的问题吧。情绪,对大脑的构造来说,就是对输入信息的再次反馈。
我在这里讲的既不是歪理也不是极端的理论。只要我们将大脑看做一个输入输出的装置——也就是计算器的话,一切就会理所当然。因为人们平常不这样想,所以将大脑的运作看成一次方程式会让他们觉得有些不适应。人类总是认为自己的大脑是更高级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地说,人的大脑只不过是一个计算器罢了。
-
-
[https://www.renzhisiwei.com/renzhisiwei/view175.html

傻瓜的围墙
- 更新日期:2024-02-27 08:18:03
- 查看次数:19
- 点击链接下载: https://pan.xunlei.com/s/VNkEzSb3vJFu5co0TUTwVx0mA1?pwd=dksm#
摘要:生孩子过程的记录片播放给北里大学药学部的学生观看。 在药学部里面,女生占了六成,比较多。当我询问学生们观看这个节目后的感想时,得到的结果非常有趣。男生和女生的反应截然不同。